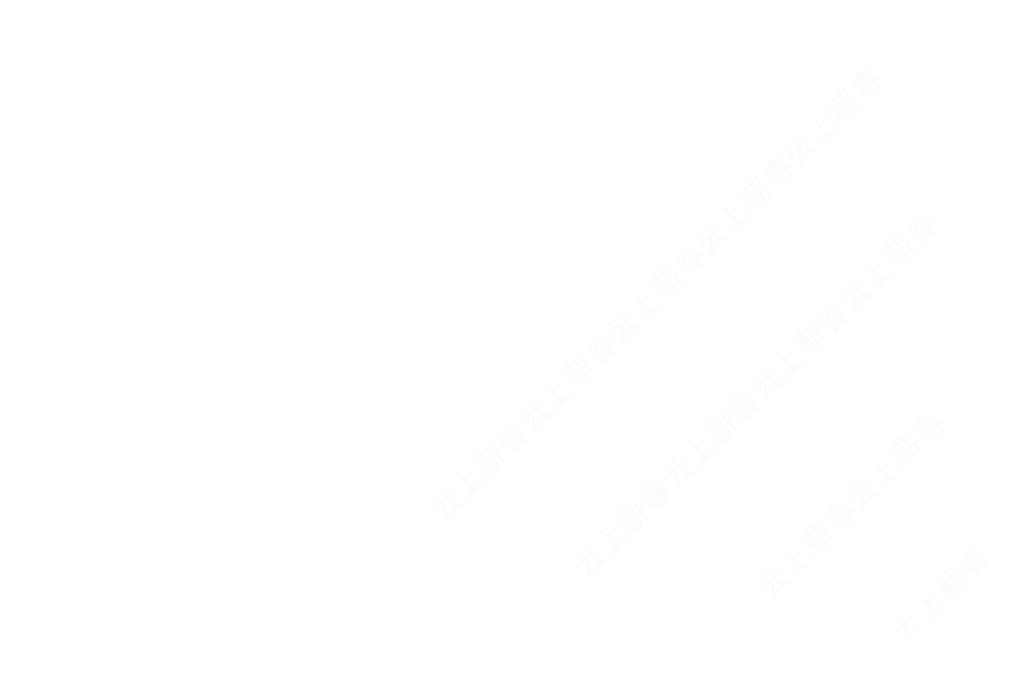一抬头,粉白娇嫩的桃花缀满枝丫。错落有致的枝条向四周伸展开来,宛如一把撑开的美丽大花伞。嗡嗡的蜜蜂在此间流连忘返。天空蔚蓝,微风轻拂,阳光和煦,花香扑鼻而来。我站在桃花下,竟有些怀疑自己此时是否又在梦乡里。明明记得现在已入夏季了,桃花也已结成桃果了,怎么这里的桃花未曾凋谢却花开正艳呢?为了弄清真假,我下意识地抬起右手放在前额遮住直射的阳光,眯起双眼寻觅那熟悉的天空,熟悉的房屋、道路。用鼻子使劲去嗅探那熟悉的气息,竖起双耳去搜寻那熟悉的声音。我看见满树的桃花——红的,白的,娇艳而不夺目,熟悉又亲切。耳边响起的始终都是蜜蜂热闹的,喧腾的,乐此不疲的快乐歌声。我甜甜地笑了,终于憋不住笑出声来。哦!又是在梦里。一个真实的同桃树有关的不愿醒来的梦。

梦里的桃树,梦里的我,梦里的情境,它们是我人生中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听父亲说,一九八三年,爷爷奶奶用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微薄积蓄,带领亲友建造了家里的第一所新房子。白墙黑瓦,窗明几净,院落别致宽敞。就在一家人欢欢喜喜庆祝乔迁新居的时候,我“哇哇……”地哭着降生了。隔壁教书的老先生便借着焕然一新的房屋赐给了我一个与众不同的又有些奇怪的名字——焕新。最疼爱我的爷爷,为了我日后能有个解馋的零嘴,上山砍了上好的木柴,天不亮就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县城去卖。卖柴换得钱后,买回来不少的果苗。有桔苗,犁苗,有枣秧,有栀子花秧。买得最多的是桃秧。爷爷在家门口院前空地左右各栽一株桃,让桃做了守卫将军,守护着依次排列的枣树,桔树,犁树,栀子花那些士兵。

桃树一年比一年高,我也一年比一年大,我们似乎都在暗暗较劲看谁能胜过谁。显然地,在竞争谁长得更高更大的这件事上,我是个十折不扣的输家。当桃树上结出又红又大又甜又酸的桃子的时候,我只能站在树底下,歪着头仰着脖子,伸长了小胳膊,却连桃树叶子都摸不着,小嘴馋得直流口水。只要树上还有桃,我每天就会光顾它许多次。哪怕是吃饱了饭,还是会不由自主地站到桃树底下,仰望着它,就像仰望彩色的星空。我转着圈去数那些可爱的桃星星, 好像上了瘾。那些桃树,在物质贫乏的我的童年里,不仅给了我最好的美味,而且给了我一个快乐自由的精神乐园。有很多次,那似乎仍可回味的桃果在我的齿间清晰地萦绕,甜甜的,酸酸的,一波又一波,在心头荡漾开来。

“傍晚时分,落日的余晖照射在桃树上,仿若给桃果抹上了胭脂。此时,远远看去,像是一个个小红灯笼挂在桃树上,十分地醒目。路过它身旁的人,总忍不住驻足抬头观望……”这是我小学时写过的一篇作文,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表扬了我。而我明白,之所以这篇作文的得到老师的肯定,是因为桃树在我心中是极美极暖的,运笔自然就多了很多真挚的情感。

时隔多年,我依然愿意再次提笔续写我的老桃树。除了对桃树不变的喜爱,更多的是感激和怀念。我发自肺腑地感激那位在班上念我作文的启蒙老师。是他的肯定激发了我对文字的喜爱,让我明白了心里的话不仅可以说出来,唱出来,还可以将它们付之于文字。文字是心灵最好的滋养剂。它们让我半生乃至一生的心灵变得充实而愉悦。当然,我也非常感激门前那棵老桃树。此刻,我反复翻看在家乡拍摄的照片,怀念之情自心底涌起。我怀念在那满天繁星的夏夜,奶奶坐在桃树下的凉椅上,轻轻摇着她那把大蒲扇,神情亲切怡然。爷爷坐在桃树正对的大堂内,拿着他的小木烟斗,在桌角轻轻一敲,倒出烟灰,又两指捻一小撮烟丝慢慢揉成团,按进烟斗里,划火柴点着了,然后深吸一口。爷爷那慈祥而略带微笑的脸在忽明忽灭的烟雾里若隐若现,神情悠然自得。

在阳光恰好的农闲时节,母亲喜欢带着她的针线竹篮坐在桃树底下和大娘大婶们一起纳鞋底,织毛衣,说说笑笑,她们的脸上总流淌着桃花一般的温柔,她们说话的声音也是那么年轻动听。蛙声片片,蝉鸣阵阵,栀子花香弥漫。在萤火虫满天飞的夏夜,桃树底下又是热闹非凡的景 象。左邻右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站的站,坐的坐,一起守着刚流行的彩色电视,看得目不转睛。孩子们有追逐嬉闹的,有聚精会神看电视的,有追着萤火虫满大路跑的,唯有桃树静静注视着这一切一言不发。那一切平常的过往,每每回想起来,总是让我倍感温暖。老师的恩情,亲情的呵护,和谐的邻居,童年的快乐,桃树下的生活,一切都是那么简单、质朴、纯真、快乐,怎叫我不怀念呢?

2003年的春天。家门前的桃树依然迎春吐蕊,而20岁的我却踏进了一家工厂的大门。每个月只有两天固定的休息日,其余的每一天几乎都要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工资计件,多劳多得。为了能多积攒些学费,为了能早日重返校园,在20岁这个人生最好的年龄,我像个机器人一样运转在熟悉的电动机旁。日子虽然辛苦,但我的心里始终充满了希望。
就在那年的某一天,我打电话回家,父母同我说隔壁的叔叔打算向我借钱建房子。我拼命上班攒钱就是为了能早日重返校园,可是年轻的我没有吐露我内心的真实想法,而是赌气说了一句:“有钱借给别人建房子,为什么不自己建呢?我回到家连个像样的房间都没有。”

就因为这一句话,父母在挂了电话之后,真的商议起建房子的事。他们一声不响地就拆了我出生时修建的老房子,然后才打电话通知我。我在电话里问:“我的桃树呢,你们把它栽倒哪里了,它还能活吗?”不知为什么,我关心那棵桃树的命运竟然胜过了我自己的命运。淡淡的月光,陪着我流了好几个晚上的泪。我的梦,我的心愿,依然存在。只是那颗老桃树,它将会永 远地离我而去。
许多年过去了,关于那棵老桃树,已不再有人轻易提起。父亲在2003年房子修建好后,或许是为了弥补失去老桃树的缺憾,又在新房子的门前,也左右各种了一棵新桃树。两棵新桃树,一棵栽活不成功,一棵数十年来竟没结过一个桃子。别人都说:“都不结桃,还留着干嘛?”父亲说:“不结桃没关系,但它开花好看,再说留着还能纳荫乘凉呢!”我想,父亲也许同我一样,都对桃树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吧。桃树不仅让我想起爷爷的疼爱,想起我的语文老师,也让我始终用一颗感恩的心对待人生。
老桃树,我想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