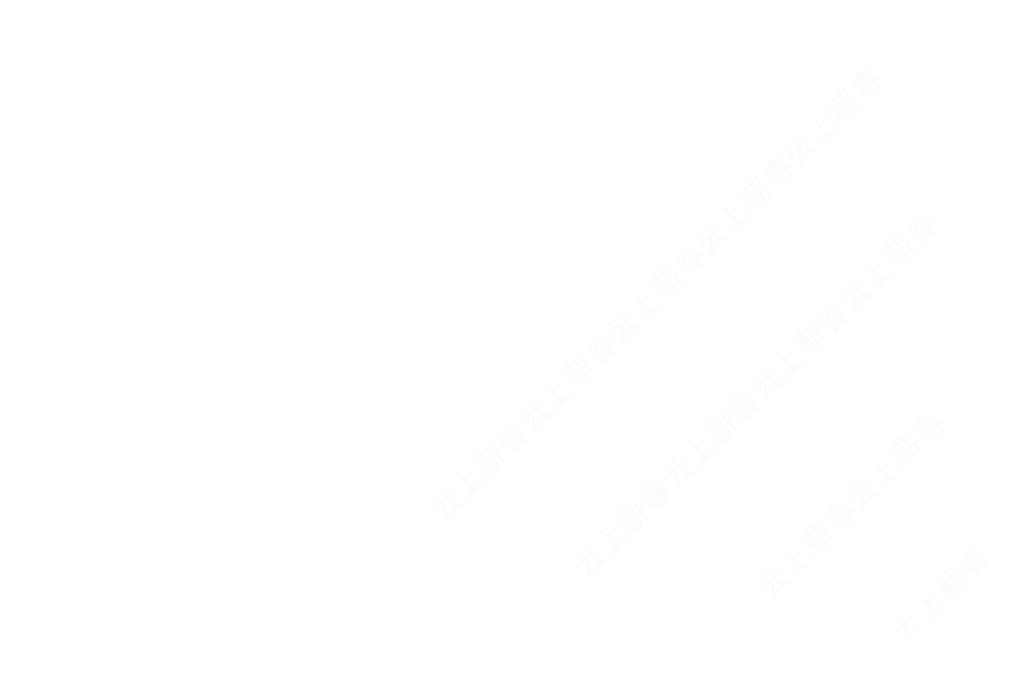三十岁这一年的春节回故乡达城去,是为了给在七十九岁上去世的伯父送葬。因为那还是在新年月半里头,所以就在家乡停留了一个周。
只是不想,几年没有回故乡的自己,就那么意外地、再一次地感受到了内心的脆弱和回不去的忧伤。
因为读书的缘故,十九岁不满离开蕲春;然后毕业参加工作,回去的次数就越发地少了起来;甚至是在后来的好几年里,都不再回去了。一来是因为工作学习的繁忙,二来是因为年岁渐长,开始理解到了生活的庞杂和生存对比的焦虑。
所以,我反倒是越发地害怕起回故乡了。
这种难以言说的心绪,并不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而是更多地感到自己的存在之于故乡的人们,仿佛就成了一种隐约的迷茫。而真实的情况却是自己在大多数的时候,即使是受了某些委屈,又或者是和他们一样对生活感到迷茫,也是不愿意让其一丝一毫表露给故乡的。
因为,故乡的孩子们还在和自己一样地努力着,我除了用沉默去表明自己还在坚持着,似乎是表达任何其他的都是不好的。因为,生活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是没有对比意义的;但我们的努力的意义,却始终是一样的,那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
大年初九的上午,接到伯父的丧报;大年初十的早上六点半,赶到县城漕河,正是黎明拂晓的时刻,远方的天际正在燃烧起大片的朝霞。
天气很冷,可我很激动,因为有好多年都没再回过头来好好看一看了,也包括这个自己生活了将近七年的小县城。
坐在车窗边守了整整一个晚上,火车一登上进城的西河驿铁路桥,我的心情就开始汹涌了起来。紧跟着进入眼帘的就是铁路轨基下的建材城,如今我的一个好朋友在那里经营着一家灯饰城。
火车还没靠站,我就赶紧叫醒了卧铺席上的妻子来;下得车来就更加地激动了,任凭妻子揉着惺忪的睡眼,跟在后头嚷着要我走慢一点儿。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仿佛,每一眼都是那么的珍贵,在我漂泊在外的十年多里,脑子里边闪现过无数次的那些场景,只是为了在这每次还乡的短暂间隙里,好好地再去确认一遍。啊,这就是故乡,这就是那个让我在外头心心念念的故乡。
火车站广场建起了架空层,原来的下沉式广场变成了满布绿植的微地形公园。虽然是变得有些陌生了,但这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的四周依然是那样的熟悉,并且是变得更加的好了。
天气很冷,但我很激动,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也不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只顾着指给妻子看那曾经熟悉的一切,从火车站广场一直到四路口,然后又拐上市府大道。那一路有我少年时代的同学家,有我办升学宴的新天地大酒店,还有交通局里边的高中班主任家,以及藏在四路里头的漕河镇中……
我不知道正当其时的自己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在为妻子讲述着这过去的一切,以及到现在仍为我守候着的点点滴滴,尽管我已经是守在车窗前,对着寂静的寒夜一整个通宵了。
回到家里,那里正是红楼宾馆。此时的酒店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样子了,正在改造中的酒店大楼被旁边新建的棕盛广场相衬得是那么的不起眼,而它也曾是县城里最繁华的一个中心地点。
回到家乡达城,待了两天,给伯父送上山去,就又带着第一次来故乡的妻子去了外婆家。心情十分的复杂,似乎,真的就是和从前不再一样了,那便是不能再和小时候一样甩下书包在满村子里边打闹,什么都可以不顾不管……
可是没有,我和妻子也只是和外公外婆待了一小会儿,然后赶着去县城的末班车,回到漕河,去妈妈上班的梁记粥铺接她下班。
回漕河的车子上,妻子因为疲惫,一上车就睡了过去,我却是对着四合的暮色久久不能平静,而难道长大了就必须该这样么?这让我很难受。
汽车从蕲春和浠水交界的丁字路口出发,沿着我少年时期走过无数次的这条路往漕河来。临到柏条铺的那条去到老家许家山的村子里的岔路上,无意中又看见了小堂哥开着车子去他中午安葬的父亲坟上,心中不禁又是一番酸楚。他少年离家,留下鳏居的老父亲在达城街供销社为他守着一个家。然后在他四十岁的今年春节,把他那瘫痪五年去世的父亲和他那早逝二十几年的母亲合葬在了一起,却是要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让他在丧父之余,还受了许多委屈。
某一刻,我只觉得自己是那么的脆弱,回到县城漕河才发现,父亲已经有了白发;母亲的身形,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得臃肿;伯父葬礼上满座的乡亲们,仿佛是一瞬间就花白了头发……而我离开家乡去才十年多一点啊!为何这一切并不曾和自己所想象的一样,在为自己保存着原来的亲切模样?
大我两岁不到的姐姐,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同辈的弟弟妹妹们,依然还是孩子般的模样。而这一切又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在悄悄改变着?那就是为何我们这一辈的孩子们还没来得及长大,而那些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哥哥姐姐们和那些在自己的印象里边从未改变过的大人们,却是要一下子变老了起来?
这令我很难受,仿佛,自己一直不愿改变的执着是不会有任何意义的。就如同进入三十岁的自己,在他们面前强调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却是要惹得他们的一致贬讽和嘲笑一样;就如同再次抱着年迈的外婆,看见她浊泪横流的一刻,我才发现她竟是如此的羸弱和瘦小,而自己是再也不能像小时候一样,搬个小板凳依偎在她的怀里了……
这令我很难受,仿佛这一切都在指责着我的不愿长大,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警示着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了。可又为何,我并不觉得自己已经长大?甚至,在下火车的一刻,在与亲人们重逢的一刻,还有那在离家去的那个月圆的深夜。
我只觉得自己仍然是那么的脆弱,甚至,如果可以的话,我只愿像十几年前一样,尽情地放声大哭一场。
大年初十的黎明,到得故乡县城漕河,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去老家达城街祭奠伯父,再在次日傍晚回到县城的家中,抛开手机,和妻子带着姐姐的两个孩子玩到正月十五。
不知为何,离家前的那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躺在床上盯着亮白如昼的窗户发呆,然后悄悄起身去阳台上抽烟,心里就想到明天的这个时候,自己就该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了。
阳台外边的院子里洒满了皎洁的月光,我悄悄地打开房门绕到客厅,拨开窗帘,一点云彩也没有,硕大的月盘晶莹清亮。我的心里不由得一酸,忽地想起小时候的自己在睡不着的夜晚,总要趿着鞋子摸到爸妈的床上去,并且还是要挤在他们的中间,才能安然入睡。而这一刻的自己,也是多么地想要那样啊!即使自己已经三十岁了又怎样?因为我依然是他们的孩子啊!
那一刻,我只觉得自己是那么的脆弱,几乎就要对着窗外的月光酸湿了眼眶。然后放下窗帘走到父母房间的门前,手却僵在半空却不能把门敲响,里边正传出轻微的鼾声,侧边的房间里是睡得香甜的妻子。就又默立了半晌,回到房间里带上房门,把已经冻得冰冷的身体放回到被子里边去。
离家的正月十六早上,母亲已经去上班了,她提前给我和妻子打包好了一大堆吃的和用的,还有她在工作闲余时做下的拖鞋,姐姐赶过来为我们做早餐。然而因为时间的紧迫,我和妻子放下碗筷就往火车站赶。
临出门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就是一酸,因为我知道中风了的父亲,正欲言又止地站在那里看着我出门去。可是,我知道自己不能回头,否则就要冲上去抱住他大哭一场。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一切是为什么,为什么自己会继续这无休止的漂泊和寻找;又为什么要明明就知道自己一刻也没有放下过,却依然是要假装坚强地让他们以为自己从不曾把这一切放在心上。
可我知道,我唯有勇敢地向前走,去到了更远的远方,才能在他们的心里种下更加坚定和灿烂的希望。因为,我能感应到,那夜的月光也一定是照在了父亲的心上。
(ShakespeareS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