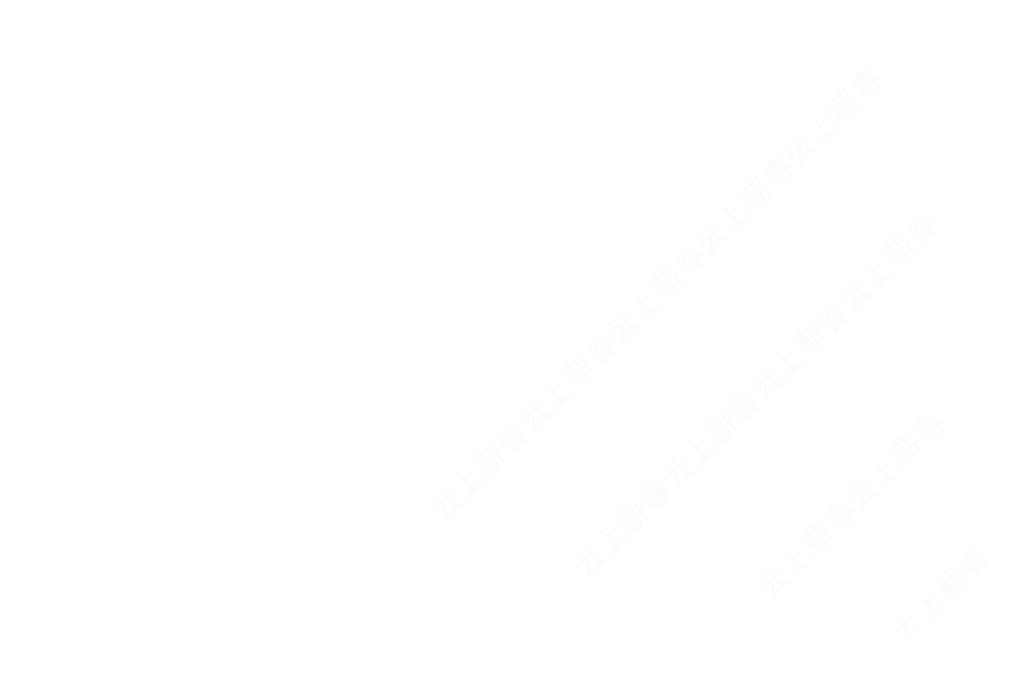дёҖзүҮеңЈеңҹпјҢзҺүе…°иҠұејҖ
ж–Ү/еӨҸжў“иЁҖ
еңЁеҢ—дә¬зҡ„жҹҗдёҖдёӘйҷўеӯҗпјҢдёҖдёӘдәә们并дёҚеӨӘе…іеҝғзҡ„дёҚиө·зңјзҡ„дёҖдёӘйҷўеӯҗпјҢжңүжҲ‘и®ёеӨҡеҝғд»Әзҡ„дәәе’Ңзү©гҖӮ
иҝҷдёӘйҷўеӯҗеқҗиҗҪеңЁеҢ—дә¬жңқйҳіеҢәпјҢиҝҷдёҖзүҮең°еҢәжңүдёҖдёӘжһҒеҘҪеҗ¬зҡ„еҗҚеӯ—пјҡиҠҚиҚҜеұ…пјӣиҖҢиҝҷдёӘйҷўеӯҗпјҢеҲҷеҸ«йІҒиҝ…ж–ҮеӯҰйҷўвҖ”вҖ”дёҖдёӘи®©и®ёеӨҡи§Ҷж–ҮеӯҰеҰӮз”ҹе‘Ҫзҡ„дәәд»°ж…•пјҢеҗ‘еҫҖзҡ„ең°ж–№гҖӮ
жҲ‘пјҢе–ңж¬ўеҸ«еҘ№йІҒйҷўгҖӮ
еҘ№жһҒе°ҸпјҢдҪҶеҚҙжңүдёҖз§ҚзҘһеҘҮзҡ„йӯ”еҠӣгҖӮи®©дәәдёҖйқ иҝ‘еҘ№е°ұдјҡиӮғ然иө·ж•¬пјҢй«ҳеұұд»°жӯўгҖӮжҜҸж¬Ўи§Ұж‘ёеҘ№пјҢжҲ‘жҖ»иғҪж„ҹи§үеҲ°дёҖиӮЎжө“йҮҚгҖҒејәеӨ§зҡ„ж–ҮеҢ–еә•ж°”пјҢд»ҝдҪӣжңүдёҖеқ—жҡ—иҮӘеҸ‘еҠӣзҡ„зЈҒй“ҒпјҢдәҺж— еЈ°ж— жҒҜгҖҒж— иЁҖж— иҜӯд№ӢдёӯиөӢдәҲжҲ‘жҖқжғізҡ„зҒ«иҠұпјҢзҒөж„ҹзҡ„еҘ”и…ҫе’Ңи·іи·ғгҖӮ
дәҢ0дёҖдә”е№ҙеӨҸеӯЈпјҢеҚ‘еҫ®зҡ„жҲ‘第дёҖж¬Ўиө°иҝӣиҝҷе„ҝпјҢж»Ўеҝғж¬ўе–ңгҖӮжҲ‘дёҖиә«зҙ иЎЈпјҢз«ҷеңЁйІҒиҝ…е…Ҳз”ҹй«ҳеӮІзҡ„еӨҙеғҸдёӢпјҢдёҖиҪ®жңқйҳіе–·и–„иҖҢеҮәпјҢе®ғзҡ„е…үиҠ’жҙ’иҗҪеңЁжҲ‘зҡ„зңјй•ңзүҮдёҠпјҢи®©жҲ‘жө‘иә«йҖҸдә®гҖӮ
иёҸдёҠеӨ§й—ЁеүҚзҡ„еҸ°йҳ¶пјҢжіЁи§ҶзқҖйӮЈдёӘй“ңжүӢеҚ°пјҢжҲ‘еҸҢжүӢеҗҲеҚҒпјҢдёҖеҝғ敬ж„ҸпјҢеҝғеҝөпјҢеҮ з»ҸжіўжҠҳпјҢз»ҲдәҺиө°еҲ°дәҶе…Ҳз”ҹ们йқўеүҚгҖӮжҲ‘дёҚж•ўе“ӯпјҢжҖ•жіӘж°ҙйҮҢжЁЎзіҠдәҶе…Ҳз”ҹ们зҡ„ж ·еӯҗпјҢдёҚиғҪжҠҠеҲҮе®һзҡ„з»ҸеҺҶжё…жҷ°зҡ„иҗҪж•°гҖӮжҲ‘жӣҙдёҚ敢笑пјҢеӣ дёәе…Ҳз”ҹ们дёҖзӣҙеңЁжўҰзҡ„ең°ж–№пјҢжҲ‘жҖ•еЈ°йҹіжғҠйҶ’дәҶиҝҷдёҖеңәеҶ…еҝғзҡ„еҪ’е®ҝпјҢжү“з ҙдәҶжјӮжҙӢиҝҮжө·зҡ„еҜ»и§…гҖӮ
жҲ‘иҰҒйқҷдёӢеҝғжқҘпјҢе®үйқҷзҡ„еҺ»иҝҪеҜ»жҲ‘жүҖжғіиҰҒзҡ„гҖӮ
еңЁиҝҷдёӘжһҒе°Ҹзҡ„йҷўеӯҗйҮҢпјҢжҲ‘еҜ»еҲ°дәҶжңұиҮӘжё…гҖҒйғӯжІ«иӢҘгҖҒиүҫйқ’гҖҒиҖҒиҲҚгҖҒеҸ¶еңЈйҷ¶зӯүж–ҮеӯҰе·ЁеҢ зҡ„йӣ•еғҸпјҢ他们жҲ–з«ҷз«ӢпјҢжҲ–з«ҜеқҗпјҢжҲ–жІүжҖқпјҢжҲ–иҝңжңӣпјҢиүҫйқ’пјҢжүӢеӨ№зқҖйҰҷзғҹпјҢеҮқжҖқиҝңзңәпјҢзҘһжғ…жңүеҮ еҲҶеғҸе№ҙиҪ»ж—¶зҡ„жҜӣжіҪдёңпјӣйғӯжІ«иӢҘжҢҜиҮӮй«ҳе‘јпјҢжҝҖжғ…ж»ЎжҖҖпјӣжңұиҮӘжё…ж·ұжғ…еҮқжңӣзқҖйқўеүҚзҡ„иҺІиҠұпјӣжӣ№зҰ№гҖҒиҖҒиҲҚгҖҒеҸ¶еңЈйҷ¶дёүдәәпјҢеқҗжҲҗдёҖжҺ’гҖӮиҖҒиҲҚеқҗеңЁжӨ…еӯҗзҡ„дёҖдҫ§пјҢдёҖж”Ҝж–ҮжҳҺжүӢжқ–ж”ҫеңЁи…ҝиҫ№пјҢи„ёдёҠжҳҜдёҖиҙҜзҡ„е№іе’ҢдёҺе®үиҜҰпјӣжӣ№зҰәз«ӢдәҺжӨ…еҗҺпјҢиҘҝжңҚзҡ„жүЈеӯҗжҳҜж•һејҖзҡ„пјҢдёҖеүҜжҙӢжҙҫзҡ„жү“жү®пјҢиЎЁжғ…жІүй»ҳпјҢжҷҡе№ҙзҡ„жӣ№зҰәеӣ еҶҷдёҚеҮәж»Ўж„Ҹзҡ„дҪңе“ҒпјҢиҜҙжӯ»дёҚзһ‘зӣ®пјҢеҸҜд»Ҙжғіи§Ғе…Ҳз”ҹзҡ„з—ӣиӢҰпјӣеҸ¶еңЈйҷ¶пјҢеҲҷз©ҝзқҖй•ҝиЎ«пјҢеңҶеҸЈеёғйһӢпјҢй•ҝй•ҝзҡ„зңүжҜӣдёӢжҳҜе”ҮдёҠжө“еҜҶзҡ„иғЎй«ӯпјҢжҲ‘з”ЁжүӢж‘ёдәҶж‘ёд»–зҡ„иғЎеӯҗпјҢ笑дәҶгҖӮ
иҖҢеңЁеҸҰдёҖдҫ§пјҢеңЁжө“жө“зҡ„ж ‘дёӣдёӯпјҢеҶ°еҝғе…Ҳз”ҹзҡ„дёҖе°Ҡйӣ•еғҸйҡҗдәҺе…¶дёӯпјҢе…Ҳз”ҹдёҖиә«жҙҒзҷҪпјҢз«ҜеқҗеңЁдёҖеқ—еұұзҹід№ӢдёҠпјҢжҳҜе№ҙиҪ»ж—¶еҖҷзҡ„ж ·еӯҗпјҢеүӘзқҖйҪҗйўқзҡ„зҹӯеҸ‘пјҢдёҖеүҜж–Үиүәйқ’е№ҙеҘіеӯҗзҡ„иЈ…жү®гҖӮеҘ№еҸіжүӢжүҳзқҖдёӢйўҸпјҲkД“пјүпјҢиӮ©жҠ«дёҖ件薄衫пјҢиЎЁжғ…еЁҙйқҷгҖӮйӣ•еғҸзҡ„и…ҝиҫ№пјҢиҝҳйӣ•зқҖдёҖеҸӘиҠұ瓶пјҢйҮҢйқўжӯЈжҸ’зқҖдёҖжқҹйІңзәўзҡ„зҺ«з‘°пјҢдёҚиҝңеӨ„иҝҳжңүдёҖеқ—зҷҪзҹіпјҢеҲ»зқҖе…Ҳз”ҹзҡ„жүӢиҝ№пјҡвҖңжңүдәҶзҲұе°ұжңүдәҶдёҖеҲҮгҖӮвҖқ
иө°иҝҮеҶ°еҝғе…Ҳз”ҹйӣ•еғҸпјҢжҲ‘жіЁж„ҸеҲ°дәҶд»–пјҢеңЁжүҖжңүдәәйҮҢйқўпјҢе”Ҝжңүд»–пјҢеңЁдәәзҫӨдёӯпјҢжҳҫеҫ—з–Іжғ«дёҚе ӘпјҢд»–зҡ„иғҢз•Ҙз•ҘдҪқеҒ»пјҢдјјд№ҺжңүдёҖз§ҚйҮҚеҺӢпјҢеҸҲдјјд№ҺжңүдёҖз§ҚеӣҪ家е’Ңж°‘ж—Ҹзҡ„иҙЈд»»пјҢеҺӢеҫ—д»–еҫ®еҫ®еҗҲзқҖи…°пјҢеҘҪеғҸиғҢиҙҹзқҖеҚғж–Өзҡ„йҮҚйҮҸгҖӮд»–зҡ„еҸҢжүӢиғҢеңЁиә«еҗҺпјҢиә«дҪ“еүҚеҖҫпјҢд»–зҡ„и„ёеҲ»ж»ЎйЈҺйңңпјҢд»–зҡ„йһӢеёғж»ЎйЈҺе°ҳпјҢд»–дёҚеғҸжҳҜдёҖд»Јж–ҮеқӣеӨ§е®¶пјҢжӣҙеғҸжҳҜдёҖдҪҚжҷ®жҷ®йҖҡйҖҡзҡ„иҖҒдәәпјҢдёҖдҪҚеҚ•з°ҝпјҢеҝ§йғҒзҡ„иҖҒдәәпјҢд»–зҡ„йЈҺе°ҳд»Ҷд»ҶпјҢд»–зңјзҘһдёӯйҖҸйңІеҮәзҡ„еҜ№еӣҪ家зҡ„еҝ§иҷ‘пјҢеҜ№ж–ҮеӯҰзҡ„жҖқиҖғпјҢи®©дәәйҡҗйҡҗеҝғз–јгҖӮ
йҳіе…үиҗҪдёӢжқҘгҖӮдё–з•Ңйқҷи°§дёҖзүҮгҖӮ
жҲ‘ж·ұж·ұеҮқи§ҶиҝҷдҪҚиҖҒдәәпјҢд»ҝдҪӣзңӢеҲ°ж–ҮеӯҰзҡ„е№ҝеҚҡе’Ңжө©зҖҡпјҢзңӢеҲ°ж–ҮеӯҰзҡ„е°ҠдёҘдёҺдҪҝе‘ҪгҖӮ
дҪңдёәеҗҺжқҘиҖ…пјҢжҲ‘иҰҒж°ёиҝңи®°дҪҸд»–вҖ”вҖ”е·ҙйҮ‘гҖӮ
еҲқеӨҸзҡ„дёҖдёӘжё…жҷЁпјҢжҲ‘жҸҗзқҖ笔记жң¬з”өи„‘жІҗжөҙзқҖеӨ§ең°йҮ‘иүІзҡ„йҳіе…үпјҢеқҗеңЁд»–иә«еҗҺзҡ„еӣҫд№ҰйҰҶйҮҢдҝ®ж”№зқҖиҮӘе·ұзҡ„дҪңе“ҒпјҢйӮЈдёҖеҲ»пјҢжҲ‘зҡ„еҶ…еҝғжҳҜд»ҺжңӘжңүиҝҮзҡ„е®үйқҷжҹ”е’ҢпјҢжҲ‘иҪ»иҪ»ж•Іжү“зқҖжҜҸдёҖдёӘж–Үеӯ—пјҢеғҸиҪ»иҪ»жҠҡж‘ёжҜҸдёҖдёӘеӯ©еӯҗзҡ„еӨҙйЎ¶пјҢ他们笑зқҖй—№зқҖпјҢд»ҺжҲ‘зҡ„жүӢжҢҮдёӢи°ғзҡ®ең°жәңиө°гҖӮи“Ұ然пјҢжҲ‘жғіиө·д»–жӣҫз»ҸиҜҙпјҡвҖңжҲ‘з”ЁдҪңе“ҒжқҘиЎЁиҫҫжҲ‘ж— з©·ж— е°Ҫзҡ„ж„ҹжғ…гҖӮеҰӮжһңжҲ‘зҡ„дҪңе“ҒиғҪеӨҹз»ҷиҜ»иҖ…еёҰжқҘжё©жҡ–пјҢжҲ‘е°ұеҚҒеҲҶж»Ўж„ҸдәҶгҖӮвҖқ
жҲ‘еӨҡд№ҲеёҢжңӣиҮӘе·ұд№ҹиғҪеӨҹеғҸд»–дёҖж ·е•ҠпјҒдёҚдёәеҗҚпјҢдёҚдёәеҲ©пјҢеҸӘжғідј йҖ’жё©жҡ–пјҢж„ҹжҒ©дёҺе–„ж„ҸгҖӮеҲ№йӮЈй—ҙпјҢжҲ‘д»ҝдҪӣж„ҹеҸ—еҲ°дәҶд»–дёҺиҝҷдәӣе…Ҳз”ҹ们зҡ„зҒөйӯӮе’Ңж°”жҒҜзҡ„еӯҳеңЁгҖӮеңЁиҝҷж–№е°Ҹе°Ҹзҡ„йҷўеӯҗйҮҢпјҢ他们зҡ„зҒөйӯӮдјјдёҖеүӮиүҜж–№пјҢжІ»ж„ҲжҲ‘еҜ№ж–ҮеӯҰгҖҒеҜ№з”ҹе‘Ҫзҡ„жүҖжңүз—…жӮЈгҖӮ
他们дёҺйІҒйҷўдәҺжҲ‘иҖҢиЁҖпјҢж— з–‘жҳҜдёҖдёӘеә„дёҘзҡ„иұЎеҫҒгҖӮ
жҲ‘ж·ұзҲұйІҒйҷўпјҢжӣҙж„ҹжҝҖйІҒйҷўгҖӮ
жҲ‘ж·ұзҲұеҘ№иҝҷйҮҢз”ҹе‘Ҫж°”жҒҜйҖҸиҝҮйўңиүІжІүйғҒзҡ„йӣ•еғҸпјҢзҒ«з„°дёҖиҲ¬еңЁж—¶з©әдёӯдј йҖ’ пјӣжҲ‘ж„ҹжҝҖеҘ№и®©жҲ‘зңӢеҲ°дәҶжӣҙй«ҳиҝңжӣҙе№ҝйҳ”зҡ„ж–ҮеӯҰеӨ©з©әпјҢи§Ұж‘ёеҲ°дәҶжӣҙеҺҡе®һжӣҙе…үж»‘зҡ„ж–ҮеӯҰиҙЁж„ҹпјҢеңЁеҘ№иҝҷйҮҢпјҢжҲ‘зҡ„еҝғеҸҳеҫ—ж— жҜ”е®үйқҷжҹ”йЎәпјҢж–Үеӯ—дёҚеҶҚзӢ°зӢһз…ҺзҶ¬гҖӮ
дҫқзЁҖи®°еҫ—пјҢйӮЈеӨ©жҲ‘зҰ»ејҖж—¶пјҢд»Ҙж–ҮеӯҰзҡ„еҗҚд№үиұӘжғ…дёҮдёҲең°иҜҙпјҡвҖңиҜ·з»ҷжҲ‘еҚҒе№ҙж—¶й—ҙпјҢжҲ‘дёҖе®ҡеҶҚжқҘгҖӮе“ӘжҖ•и·ҜдёҠе°ҳеңҹйЈһжү¬пјҢе“ӘжҖ•и·ҜдёҠиёҸиө·йЈҺйңңпјҢе“ӘжҖ•жҲ‘еҚҒе№ҙеҗҺзҡ„жҲ‘жүҝеҸ—зқҖз”ҹжҙ»дёҠжңүиҖҒдёӢжңүе°Ҹе·ЁеӨ§зҡ„йҮҚйҮҸпјҢе“ӘжҖ•еҚҒе№ҙеҗҺзҡ„жҲ‘иў«дё–жҖҒзӮҺеҮүзЈЁж“ҰжҢӨеҺӢзҡ„еҫҲз—ӣиӢҰпјҢжҲ‘дҫқ然дјҡеҶІзқҖиҖҖзңјзҡ„е…үжҳҺпјҢеҘ”еҗ‘жҡ–ж„ҸеҰӮжҳҘзҡ„иҝҷйҮҢгҖӮвҖқ
дјҡеҶҷиҜ—зҡ„дҝқе®үеҸ‘еҫ®дҝЎи·ҹжҲ‘иҜҙпјҡвҖңеҰӮжһңдҪ иҰҒеҶҚжқҘйІҒйҷўпјҢдёҖе®ҡиҰҒйҖүеңЁдёҠжңҹпјҢйӮЈжҳҜзҺүе…°иҠұејҖзҡ„ж—¶иҠӮпјҢйӮЈж—¶ж»Ўйҷўеӯҗзҡ„зҷҪзҺүе…°ж‘ҮжӣізқҖпјҢж»Ўйҷўеӯҗзҡ„жё…йҰҷе’ҢжҳҘиүІдјҡи®©дәәдёҖз”ҹйғҪдјҡи®°еҫ—пјҢи®°еҫ—йҳіе…үдёӢзҫҺеҲ°еҝғз–јзҡ„жҜҸдёҖдёӘжё…жҷЁе’Ңй»„жҳҸгҖӮвҖқ
вҖңеҘҪгҖӮеҚҒе№ҙеҗҺпјҢдёҖе®ҡжқҘгҖӮвҖқжҲ‘иҜҙгҖӮ

дҪңиҖ…з®Җд»Ӣпјҡ
еӨҸжў“иЁҖпјҢеҺҹеҗҚйҷҲеҝ—еі°гҖӮ97е№ҙз”ҹпјҢж№–еҢ—и•ІжҳҘдәәгҖӮ
й…·зҲұж–ҮеӯҰпјҢеӣҪз”»пјҢжҲҸжӣІгҖӮ2013е№ҙеӯҰд№ еҲӣдҪңиҮід»ҠпјҢе…¶е°ҸиҜҙгҖҒж•Јж–ҮдҪңе“Ғж•Ји§ҒеӣҪеҶ…еҗ„еӨ§жҠҘеҲҠжқӮеҝ—гҖҒйҖүеҲҠдёҺзҫҺж–ҮйӣҶпјҢж•Јж–Үе…ҘйҖүеҗ„зұ»е№ҙеәҰйҖүжң¬еҸҠдёӣд№ҰпјҢжӣҫж•°еҚҒж¬ЎиҺ·е…ЁеӣҪеҗ„зә§ж–ҮиүәгҖҒеҲӣдҪңеӨ§еҘ–гҖӮеёҲд»ҺеҲҳеҪ©зҮ•гҖӮ
зі»дёӯеӣҪзҺ°д»ЈдҪңеҚҸдјҡе‘ҳпјҢеҢ—дә¬еёҲиҢғеӨ§еӯҰж–ҮеӯҰйҷўдҪң家й«ҳз ”зҸӯеӯҰе‘ҳпјҢгҖҠж•Јж–ҮйҖүеҲҠгҖӢ第дәҢеұҠдҪң家зҸӯеӯҰе‘ҳпјҢжӣҫд»»дёӯеӣҪйқ’е№ҙдҪңеҚҸдё»еёӯеӣўжҲҗе‘ҳпјҢж•Јж–Ү委еүҜдё»д»»пјҢдёӯеӣҪж ЎеӣӯдҪңеҚҸ第дә”гҖҒе…ӯеұҠ全委пјҢзҺ°д»»е…ЁеӣҪй«ҳж ЎеҲӣдҪңдёӯеҝғдё»д»»пјҢгҖҠж•Јж–ҮйҖүеҲҠгҖӢгҖҠй«ҳж Ўж–ҮеӯҰгҖӢгҖҠдҪң家йҖүеҲҠгҖӢгҖҠиҙөе·һж–ҮеӯҰгҖӢзӯҫзәҰдҪң家гҖ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