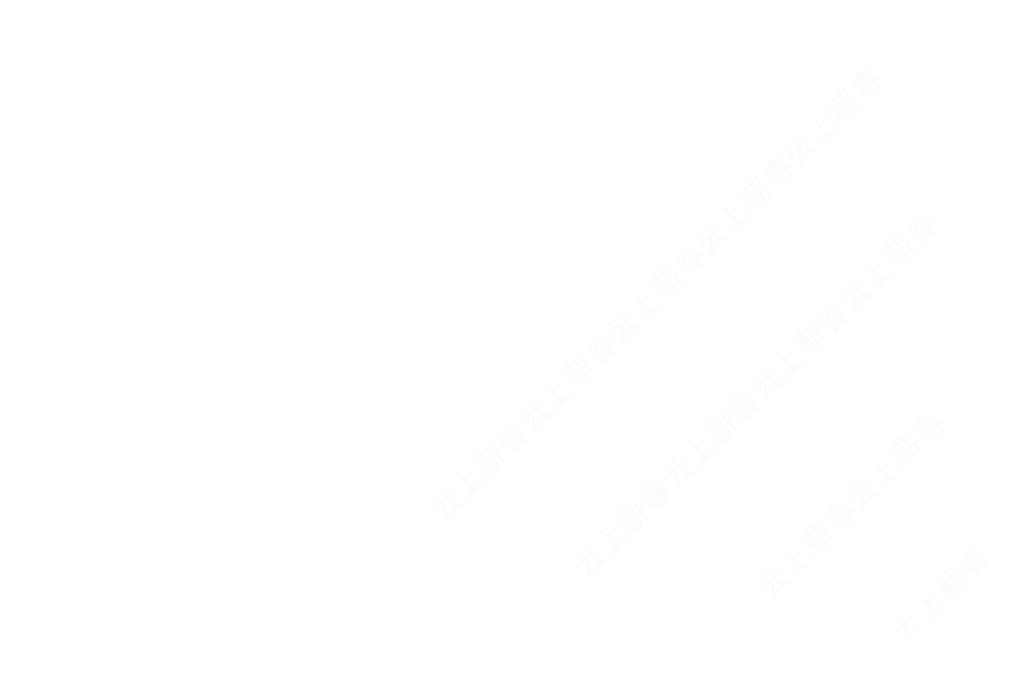我喜欢这样地活着,就算老了又如何
文/刘彩燕
越来越喜欢看戏了。咿咿呀呀,华彩丽服,寸步紧移,一招一式,都那么强烈地吸引着我。前些年,我可是很讨厌京剧的啊,我受不了它音节的拖沓,尤其受不了它一个“啊”字可以唱几分钟,嫌它慢,嫌它罗嗦,嫌它夸张,现在,我却认为这一声“啊”的高低起伏,恰似莺啼婉转,又如铁骑突出,在这样的抑扬顿挫中,那些喜怒哀乐,那些悲欢离合,就有了新的意义。有时还能闭着眼睛和着节拍,西皮流水几句,俨然是一个十足的上了年纪的戏迷。
越来越喜欢听别人讲话了。以前的我,最骄傲的事可能就是一个人在众人面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享受着众人欣赏、惊诧的眼光,享受着别人自叹弗如的表情;可现在越是人多我越是不愿意开口了,好象突然明白了言多必失,说话的人远没有听话的人舒服自在这个简单的道理。有时候听有的人说着各种梦话、空话、瞎话、大话,也不会笑话。也不喜欢和人争辩什么了,他要说是对的,就让他说去吧,我不需要让别人来承认我的观点,但我也不会随便去应和别人的观点。越来越能冷静地对待表扬和批评。我知道我没有别人表扬的那么好也没有别人批评的那么差。我很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优点和劣处,不知什么时候就真的明白了不卑不亢,而我又知道,我不是真的境界在提高,充其量,我只是一个假高尚真逃避吧。
越来越能容忍别人的吹牛。曾几何时,我是很厌恶别人吹牛的,尤其是看一个男人吹牛,看着他们忘乎所以地在那自我陶醉,我总要忍不住去揭穿事实真相,再不然就是用断然地拂袖而去来显现我的超凡脱俗和不屑一顾,可现在,我更多的像是在看一场表演,我知道了一个喜欢夸夸其谈的男人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他们渴望用那种语言上的言过其实来达到一种包装、包裹的目的,如果连这一点小小的满足都不能让别人实现,似乎也觉得自己太残忍了。
以前,我是那么地渴望了解别人,也是那么地渴望被人了解,如果别人说我不理解他,我真像做错了一件事情一样羞愧;如果被人误解,我会恼怒,会哭泣还会去一再地解释,仿佛这世界一定要互相理解才能天下太平。“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孔子的教诲。现在的我,虽说仍旧需要理解,但也能坦然地面对误解和不解。同时我更懂得了尊重,尊重和你不一样的观点,尊重和你不一样的需求。因为,一味追求大同,就会使世间少了许多斑斓。
越来越喜欢简单。不管是衣服、食物还是交往。简单一点好。衣柜里倒是有一些过去的华服,我常常会想当初为什么会购这些衣服,现在看起来不是样式过于繁复,就是面料过于精致,生活不是去赶一场一场华丽的舞会,穿不上却又不舍丢弃,远不如这纯棉的简单熨贴又舒服自在。偶尔也会想起曾经有过的呼朋引伴的日子,那个时候,怎么热闹怎么来,怎么虚荣怎么做,通讯录上冠盖满京华,可夜深人静常常却是斯人独憔悴。而现在,我基本不用通讯录,有限的几个朋友,一切信息我了然于心。我对“朋友”的定义也趋于简单,不必刻意,无需安排,犹如大浪淘沙,剩下的都如珍珠般宝贵透亮,而我也将用全部的真诚去珍藏。
“生活的最终目标是生活本身”,这是俄国作家赫尔岑说的,对我有着醍醐灌顶之效。以前总是觉得自己此生一定要干成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很多小事不屑为,很多时间看起来是在书桌边用功,其实只有自己知道,枯坐的时候多,发呆的时候多,不知所措的时候也多。
以前写文章之前也总要告诉自己要微言大义,要用文章来反映什么,来说明什么,现在才知道,我什么也反映不了,也说明不了。我的文章经不了世也济不了国。我成不了伟人,也做不了大家,但我并不是一无是处,至少我可以认真地做好自己,把每一天过好就是一种进步。我欣喜地看到自己在一点点变化:我可以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慢慢地煲一锅汤,看着那汤不断地沸腾翻滚,心里便有了无限的喜悦与盼望,渴望着那喝汤人的眼里满是脉脉柔情;可以花半个小时打一个长途电话来听母亲絮絮叨叨地说着家长里短,聊着麻将的输赢;可以长久地注视着一幅画,也可以反复地听一首歌,看一部喜欢的影片。
有时候也看到这样的画面,小伙子用万朵玫瑰来向年轻的姑娘求爱,缤纷异常,哗众异常。我就会在心底里发出一声轻叹:真正还是年轻啊,他们并不知道,万朵玫瑰并不能表示什么,真正的心悦君兮,恰如沐浴着冬日的阳光,流淌在心头的只有温暖与舒适。它不是用来炫耀的,也不是用来攀援的,它一定要落实到一粥一蔬,落实到耳鬓厮磨,那些真正的爱里,一定有着无尽的牵挂与真心的心疼。
越来越不喜欢故弄玄虚。也曾有过这样的日子,很喜欢给别人打个电话,用变了调的声音问对方:“猜猜我是谁”,如果对方猜得出便罢了,如果猜不出,那便要大呼小叫一番;如果接到这样的电话,为了配合对方的情绪及游戏的规则,猜得出也要故作猜不出状,“从Mary到Sunny和Ivory ,却始终没有他的名字”, 那个时候,要的就是这样一种欲擒故纵,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虚张声势。可现在自己给别人打电话,就是再熟悉的人也要先自报姓名,越到这个年纪就好象越能有自知之明,就知道谁也没有记住你名字的义务。现在我的学生也很喜欢和我开这样的玩笑,我却没有和他们玩游戏的心情了。他们打电话给我,不论怎样的变调我都能一下子听出来,因为我对声音有着出极的敏感,他们就改用短信,回家以后用一个陌生的号码给我发一段很煽情的话,然后不忘打上一句:“猜猜我是谁?”最后的结果往往还是自报家门,因为没有配合的游戏终归是会自己谢幕的。有一天,一个学生“怒不可遏”地对我说:“我觉得老师你真的老了,落伍了,应该歇菜了。”我却又一时没有明白“歇菜”是什么意思,看来,我真的是老了。
那天看一位长者写的有关《红楼梦》的见解,本来我是怀着颇为景仰的心情去欣赏的,孰料这位在中国文坛有了一定名望的尊者且已有些年纪的长者,谈红楼是虚,发牢骚是真,每一篇谈红楼的篇幅中总要或见缝插针或含沙射影或直呼其名地大骂或批判,大段大段地发泄着对迫害过他的人的怨恨,大段大段地宣泄着对文坛的不满,我第一感觉就是觉得这位长者这一大把年纪还没有活明白,我本以为,一个人到了须发皆白的时候,应该差不多宠辱皆忘了的,绝不会心怀不平,绝不会愤世嫉俗的。
那一天,我重感冒,全身发烫,浑身乏力,吃过药以后便躺在床上,儿子在我身边相陪。楼下小伙伴叫他的声音此起彼伏,他开始还大声地回答:“我不玩。”后来就跑到阳台上压低声音说:“我妈妈病了,我不去玩。”可是却走来走去,坐立不安,我知道儿子想去玩,但又怕我孤单不愿离开。我对他说:“你下去玩吧,妈妈想睡会儿。”他像得了奖赏一样,然后又信誓旦旦地保证只玩一会儿就回来。儿子下去以后,我感到空落落的,眼泪忽然就无声地滑落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需要一份被呵护的感觉,哪怕是被一个十岁的孩子。忽然就理解了那年母亲用生病的谎言只是为了骗我回去看看她的那种心情,当时我是那么气急败坏,而现在,我是那么强烈地想要求得母亲的原谅,所谓“返老还童”,老人和小孩的心情往往是相通的,老小老小,都需要被人捧着哄着,既然我现在应该不算小了,那唯一的解释就是我在变老吧。
曾经,我是那么害怕变老,年老在那时的我眼里,意味着满脸皱纹,意味着老态龙钟,意味着顽固退化,意味着步履蹒跚,我觉得这世上最残酷的事之一便是拿一个女人年轻时和年老的照片来对照,年轻时候无论怎么看都是一朵花,年老的时候,那不是花而是老树根。可是现在,有时候看到这样的对比照片,却对那“根”充满了敬畏,我知道我也正慢慢地向着这根迈进,但只要这根深深地扎进泥土中,它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养料,就算是被人挖了出来,作不了盆景,还可以当柴烧,至少可以温暖一双寒冬里冰冷的手吧。
“当你老了/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的眼神的柔和,/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这样美丽、悠长、哲思的句子,似穹庐,笼千年,久弥香。每读一遍,心中就对年老多了一份向往。
不追悔,不怨恨,不念旧,不羡新,不急不燥,不媚不俗,不损人也不损已,不贪恋更不妄求,这样地活着,就算老了又如何呢?

作者简介:
刘彩燕,李时珍职校教师,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2005年创办胡风文学社至今。